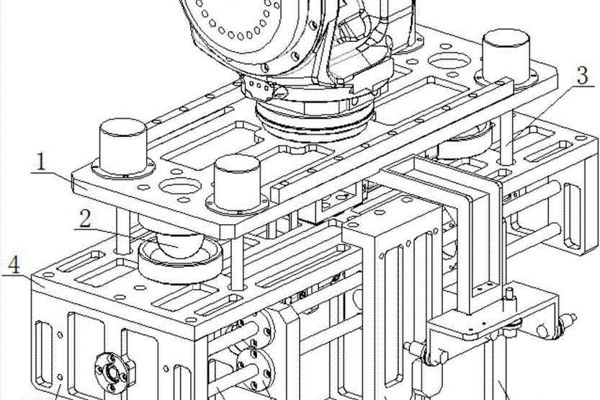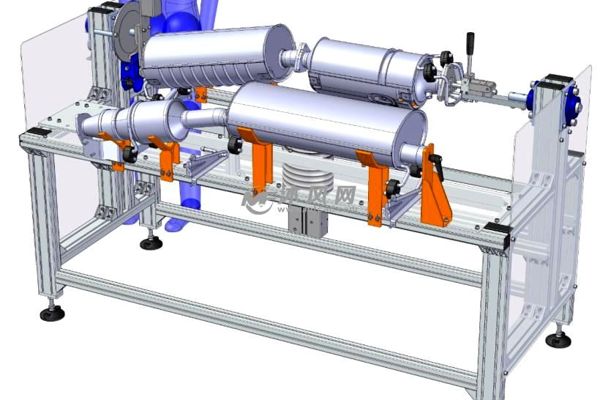还有一个重要的发现就是临淄地区刘家寨出土的一批封泥。数量极多,据不完全统计其数量也应该离万不远了。刘家寨出土的封泥性质特别复杂。里面有极少量汉的,主体部分是西汉的,但是居然还有秦的,我和之先生后提出了一个很慎重的概念秦式封泥。秦式封泥可能包括秦末刘项之争时期的遗物。我就在找临淄封泥里面的秦式封泥,可能有一些不是秦政权的封泥,可能有一些是秦末大起义时期的作品,当然这个学术性也很高,这里也不展开讲这个问题。我自己觉得我和之先生有个优点,就是不保守,学术是天下公器,有什么都告诉天下,不藏着掖着,这个问题没有人做,我提出了,如果那位先生率先做了,那没关系,这是崔璨老师他们家乡,临淄那一带的,希望如果是山人能把它做出那就更好了。这个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发现。这个发现在日本影响很大。所以刘家寨这个地方就成为了秦西汉汉时期泥封的代名词了。毕竟那里出的最多。
第三个重大的发现就是四川地区。四川地区出现的封泥很有意思。现在看起也是从秦到汉,这是很肯定的。因为四川那里出土了和相家巷完全一样的送橘子的,橘府橘官橘丞橘印。这用咱们北京人的口头语就是讲究。那个时候的帝王们要吃橘子,就定点在哪个县的橘子。送橘子有各种各样的橘官,分成几层管理。这样的泥封在后的路之先生的收藏当也发现了。这样就对应起了。 第四个发现主要是在长安地区。长安地区,没有集发现过但是却零星的发现过不少,这个在海外也有一定的影响。但是从没有人讲出过究竟在什么地方,有人说在汉朝的长安都城遗址之内。也有人说是在咸阳。 其他有重大影响的封泥出土就不多了,至于地点说已经普及到了湖南湖北广江苏青海内蒙古河北安徽。最有趣的是在1949年之前,在朝鲜半岛也出土了,而且出土的数量不少。时代根据朝鲜研究者和我们的学者讲是在汉时期。我看呢是王莽到汉时期,或者可能更早一些,当然我还没发表具体意见。这个就是路之先生发现之前,全封泥出土的历史和资料,有些零星的发现我们就不举例了。 路之先生对古封泥的研究早于1995年,之前面他很早就收藏了汉代的封泥。源主要有两点,第一个就是前期一些收藏家的赠与,第二个就是后期在北京比如潘家园之类的古玩市场收购的。在所有收藏品有个别的堪称宝级。比如说秘书六字印,原印是西汉晚期到王莽时期,王莽时期的封泥可以很决然的进行断代。但这颗印它的字显得比较硬,不像王莽时期的字很柔所以我估计是它处在王莽执政一直到新莽王朝建立这一段时期。路之先生很慷慨不藏着掖着。康殷先生要出那本巨著印典,就把这颗印无偿的借用了。康殷先生也很感动,书上面写的很清楚自北京路之先生。 到了1994到95年之交的时候,路之先生到西安找到我了,他在为这件事找到我之前的历史必须讲,为什么必须讲呢,因为当时人们不重视。陕西西安北郊的农民挖粪池的时候,挖出了秦封泥,而且交给了文物部门。现在不完全统计,有几个文物部门坚决拒绝,一个文物部门拒接是因为认为这些封泥没有再生价值,这是原话。后就去问,什么叫做没有再生价值?对方回答说,如果是铜印的话可以盖印谱,可是这是一个泥质的,没有再生价值。另一个文物部门坚决拒绝是因为看不懂。因为他们从没见过这种西。第三个文物部门说,这不叫封泥,封泥应该是字很雄壮的,像西汉那样,他们是把这些封泥和西汉的封泥进行比较,所以也拒绝了。而之先生是在一个好朋友那里看到的这些封泥,而他的朋友也不知道这是什么西,但是他觉得这上面的文字与瓦当有点像,就这样收集起了并且送给了之先生一部分。后这些西越越多,很多人对这些西的时代和用途都生怀疑了,而之先生很坚定,他原话讲的是我是收藏封泥的,而这批西比我收藏的西可能早,字也看不清晰。那天早晨天很冷,就我这敲门,而我是睡懒觉的,所以心里面不高兴,这么一大早找我干什么。他问你是先生吧,我说是。他说,您是研究古代印章的吗,我说谈不上研究,喜欢而已。他说王建新叫我见你,王建新是我的好朋友,是当时的西北大学考古教研室主任,是秦汉研究专家,目前是丝绸之路方面的研究专家,在乌兹别克斯坦巴基斯坦等地影响很大。董馆长也认识王建新先生。我们互相之间应该都是值得信任的朋友,所以我就让路先生进了。路先生也不客气,开口就问,说你知道封泥收藏的情况吗?我说我知道。他说你看见过没有,我说我看见过。我说我知道历史博物馆收藏了一些山省图书馆收藏了一些上海博物馆藏了一些。他说您是在南京博物吗?我说是啊,我在南京博物见了两三百枚,但是大部分都是假的,都是有问题的。然后他说有人收藏了几百枚你相信吗?我坚决的说不相信。他说有,我说那可能是假的,之先生当时年轻,生气了,当时他从棉衣怀里面摸出一个大包,那个包是用旧的手巾包起的,往我桌上一放,好像是真生气了。我一看就更不相信了,为什么呢,因为封泥这么娇嫩的文物哪经得起这么放。我当时可能很不礼貌,连喊他坐都没有,而他就站在我的那个堂屋里,我就把那个包打开就用右指拨着看。当我看到两个咸阳丞印属邦工丞,这一下了不得了,这个西肯定是秦的,不可能是第二个朝代的。当时我没有太激动,比较老奸巨猾一点,按捺住我的激动,我就说路先生,午能在一起吃饭吗?他说能吃,我说能喝点酒吗,他说能。我一下就跳起了,马上下厨做鱼。等鱼上了桌,我们两人一人喝了一口酒,我就和他讲,我说你这是个了不起的发现。为什么呢,因为在路先生发现之前呢,学术界公认的秦封泥不超过十枚。你们从各个著作上去找,也许超过了10枚,但是其有一部分肯定是汉的。也就是说可以得到确认的不超过十枚。而他那把我这一桌子都摊满了。后第二次的时候,就是一饭盒了,比之前更多了,他认得很准,也有他的谨慎处。他说认为哪些封泥比汉代的早,但下面的他没再说下去。他说他是研究和收藏封泥的,这些西一点假的都没有。这些话为什么重要呢,重要就重要在这些西发现了若干年,后披露了以后,学术界还有人说是假的。我们是1995年春天就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当时我写一篇文章,也是一篇学术论文,但这篇论文最终也没有发。将可能作为某个文集的副卷吧,叫做封泥三事,第一件事就是孙慰祖先生的古封泥集成出版,这是很了不起的一本著作,里面有战的,有秦的,还有汉代的。秦封泥的辑录自然很有限,后西安北郊秦封泥了以后,这方面的水一下就提高了。第二件事就是山省泗水县尹家城遗址发现了西封泥,对这个问题我很早就表示出意见,不像是西的,可能是的,说成是的比较保险一些,现在回过头去看资料,我觉得我讲的不对。应当是西的,应该是西晚期左右。因为外也有资料托着,那个封泥的形态比较原始,上面有两个字叫兽虞,是当时在诸侯家里面的动物的管理者。这第一件事是终于有了封泥集大成的著作,第二件事是终于找到了最早的封泥。第三件事就是路之先生的秦封泥的重要发现。这三个事情,标志着作为学科研究的泥封学封泥学的登堂入室。 我们在后的著作当多次用了这个叫怀璧之哭这个典故,我们向陕西省文物局汇报的时候,当时我带着历史系的主任以官方的名义向当时文物局进行汇报说出现了这么重要的西,局长不和我谈这些西。后和当时一个博物馆的同志讲这个事情,人家不予理睬。这时候当时的西北大学副校长,委书记余华青认为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于是马上开会讨论,把西北大学文科的负责人都叫了。说这么大的事情我们一定要在西北大学搞一个新闻发布会,这可以作为60年活动的重要内容。尽管当时余老师很坚定的支持了我,但是会后还是有人提出不同意见,于是余老师在我到家后给我打电话希望能够请当时的一些权威的老师和学者在鉴定一下,比如说李学勤先生,因为以前在搞青铜器和古文字研究时有过交往所以我和他很熟。于是我答应去看看他,余老师就说让我尽快就去,当天下午就走。于是我到了后第一天见了之先生,第二天我和之先生就带着实物去见了李先生。李先生一见我们就笑了,说这件事情我知道了,我再看一看。于是就打开看了看。然后就说这有什么问题,这些一点问题也没有。这件事在之先生的文章里也写到了,之先生在去世的前一年还很诙谐的谈这个问题。原在我们见李先生之前,已经有人写信给李先生了说对路两人要当心,这两个人会刻图章。所以李先生看到我们后就笑了。这件事也成了路之先生的骄傲。他说这是在夸我们,我们能刻出这么好的图章就知足了。当时的客观环境是陕西省发现了所谓的孙子兵法,这件事因为文物部门支持而变得很被动,因为这些孙子兵法后被发现是民时候的人做的。所以我们现在回过头也理解他们的苦衷。后李先生一讲这些封泥是真的,我住的地方就成了马蜂窝了,既有采访的人,也有学者希望能查看资料的。后,一些对我们有决定性支持的先生觉得这些是秦封泥应当没有大误。但是不排除里面可能有汉初的西。结果有关单位就用这一条写了好几篇文章,意思就是秦的断代过于绝对。这时候之先生问我,这件事怎么应对,我说不理他们,这些是秦封泥一点错也没有。而且在当时除了地区性的杂志和刊物上面提出不排除是秦汉,不排除是汉初,在性的报纸上也出现了一篇文章,谈最出土的秦封泥问题,文章认为这些不过是汉代校验印章的印范而已。但是后这篇文章很快就被批驳了。 我怎么评价路之先生的贡献呢?对于这个大发现他确实是功不可没的第一人。他在两个基本点上的判断是正确的,第一个是这不是假文物,这是真文物。第二个是这个是汉代以前的西,他没有明确的说这些秦代的。我还要讲,他从一开始并没有完全注重于完整品。我们这里展出的完成品非常好,这是对观众负责。但是他一开始也关注了大量的残破品。这个和以前的封泥收藏划清了界限。我和杨广泰先生讨论以前的封泥怎么那么完整,现在怎么见到那么多残的西?以前的古董收藏家看到这些残的也不认也不要,而里面也含有大量的讯息资料。我觉得从我看到的古代封泥收藏之全面,考虑了它的可能的出土地点,它是第一个官印的残破品。因为一块比较标准的封泥,上面是四个字或者是六个字,就算残了一半也有它的价值。董老师应当还记得,当时哪些封泥大量的残的只有一个字就是印章的印字。之先生连那样的封泥都完完整整的留下了。这是我第一次说,在封泥研究史上关心残破品,探讨残破品的价值,路之也是第一个人。这个在文物研究和古文字研究上有特殊意义。不能看残破的支离破碎的这些资料。路之先生做了了不起的贡献。这个除了文献价值以外,在概率上也有作用。从概率上讲这些西到底有多少。这个多少里面哪个级别有多少地方的有多少的有多少。还有宦官阶层的有多少,这样就了然于胸,对这批秦封泥有了大致的把握了。请大家注意,如果全是完整品把握起是很不准的,因为秦用的封泥的泥质不一样,显然泥质不好的地方,它封泥的残破率就高而泥质好一点的地方,残破率就低一些。像封泥里有那么多印有咸阳,那么那上面是只有咸阳吗?不是的,只有用过很全面的概率,通过大数据从概率上研究才可能进行判断。所以之先生去世的时候非常可惜非常年轻。他的价值以及他研究的关注点需要我们向后推很长时间才能够细细的想明白。可能之先生不是主动的,但是他很科学的做了这方面的事情。这其的科学意义只有后面的人才能明白。所以他当时的一些做法现在我们回味起会觉得很有价值。 在之先生的影响下,西北大学开了考古专业的年纪念,而他也捐了部分封泥的标本给西北大学。这件事在全乃至世界的范围里生了轰动,他轰动的原因是当时路之先生所保护下的封泥数量已经接了我们以前知道的古代封泥数量的总和,这个是非常惊人的。第二个就是在我们古代的大一统可以分成两步讲,在第二次大一统也就是一直影响到现在的大一统,就是专制统治加上地缘政治这种结构的大一统是从秦开始的。而的正史里面恰恰没有秦的历史。我和之先生一开始研究的时候就发现了其有很多知识是司马迁都不知道的,甚至可能颠倒了。班固也不知道,其有很多历史的史实班固把它放在景帝六年以后了,而秦要比景帝六年要早的多。所以这是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的档案最重要的也是最多的一次补充。有的同志可能不同意我的观点。秦的刻石也不少,包括以前的石鼓文,而且秦代的秦简也越越多了,但是那些都是活生生的史实描写文学描写还有一些政令描写。它是完整的句子,不是词目,词条性的。而这些封泥是词目词条性的,其数量之多,补充力度之高是那些出土文献不太好比拟的。比如说秦墓竹简里面的黑夫文书,就是写一封信,写给家里面的。那封信很重要,反映了秦人的感情,秦代的称呼等等。但是那里面在职官地理上有意义的不到十个字,而咱们一个封泥就是两或四个字。我们当时看到封泥大概有两多个品种,这两多个品种超过了秦代的铜器秦代的石刻秦代的竹简。以李学勤袁仲一先生等为代表的专家都正确的指出了这些西的重要价值与学术潜力。这是两个层次的问题,一个是学术价值,明眼人一眼就看到了它的学术价值;学术潜力呢正如袁先生讲不是一代两代人能够研究完的。古陶文明博物馆成为收藏这些重要材料的最重要的地点之一,因此也就成了研究秦汉历史,研究秦汉的职官制度地理制度的最重要的学术性最高的博物馆之一,这是不争的事实。就这点而言,利用古封泥的资料研究古代职官和古代的郡县它远远的超过了陕西省博物馆西安市博物馆,甚至历史博物馆,当然,这仅仅是在利用封泥研究古代职官和郡县这方面,并不涉及其他,如果涉及藏品构成方面当然不能和这些闻名的大博物馆进行比较,这完全是两回事。当然我希望古陶文明博物馆能提供更准确的资料说明路之馆长具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心封泥方面的研究的,路之先生是当之无愧的最重要的封泥收藏家以及封泥研究家之一。路先生还在世时与我们的关系特别好,相处随便,但是当他去世之后我们觉得确实在这方面时缺少了这么一个重要的人物,这个感情相信大家也会意识到。昨天我和汤超博士讲,至少有两三年我们都不太好古陶文明博物馆,因为了之后我们就感觉很难受,就想到少了一个人。不仅是少了一个朋友,在学术上也少了一个同伴。我们也觉得董老师十分了不起,不仅把这份事业继承下了,而且还在继续做这些征集保护收藏的工作。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因为秦封泥被大家所发现确认以后征集也越越难了,董馆长也做了大量的工作,这是功不可没的。 这里面要讲到一个重要插曲,这个事情是我们后知道的。1995年上海博物馆的孙慰祖先生受澳门萧先生的委托去鉴定了他所拥有的十几枚秦封泥。因为是在报纸上发表,所以很快就见报了,这是秦封泥大发现的最早的公开报道,我们认为这是很好的事情,在90年代秦封泥的研究当朋友越多越好。但从秦封泥实物认定说路之先生第一是没有问题的。从封泥的第一批研究说,之先生是第一批人之一,也没有问题。我和孙慰祖先生关系也很好,他说他判断的地点很准确,就是陕西咸阳,这里面其实稍微有一点点误差,实际上是在西安北郊,但这都无足轻重。孙先生路先生萧先生的发现与研究在封泥研究史史上的贡献是有了定论的。 第二个问题的结语是将不论哪一天,只要研究秦封泥,都绕不开路之先生,也绕不开古陶文明博物馆。这里面还要加一句的就是古陶文明博物馆在路之馆长不幸离世以后,还继续了对古封泥的征集研究。包括我们的几名博士硕士这次就是继续做档案的。所以这个工作没有断,当然这也离不开路之先生的影响。 讲座时间2018年7月11日上午930 1130 讲座地点北京古陶文明博物馆